初到以色列:困境中寻生机
1992年,那是一段满是苦涩与无奈的岁月,我踏上了返回以色列的旅程。彼时,13岁的老大、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还留在遥远的中国。选择回到以色列,实在是被生活逼到了绝境。我的父亲是犹太人,在二战的硝烟中逃亡到上海,在那里,我降临到这个世界。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我,母亲在我年幼时狠心离去,12岁那年,父亲也永远地离开了,我瞬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。
长大后,我在上海铜厂做着体力女工,日子虽艰苦,却也有了自己的家庭,还生下了3个可爱的孩子。然而,命运再次给了我沉重一击,丈夫决然地离我们而去。留在上海,每一个角落都承载着痛苦的回忆,仿佛空气里都弥漫着悲伤的味道。
恰逢中以正式建交,怀着逃避过往伤痛的心情,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。原以为到了以色列,会迎来新的生活,可现实却给了我重重的一巴掌。刚到以色列的日子,远比我想象的艰难。我不懂当地的语言,父亲教的古希伯来语在这里早已不再使用;也不了解移民优惠政策,要知道新移民是可以领取一笔安家费的。走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,我满心迷茫,未来的路在哪里,我毫无头绪,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下去。
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少得可怜,仅仅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。时间紧迫,我必须尽快找到赚钱的方法,还要早日把孩子们接到身边。于是,我咬着牙,开始苦攻希伯来语,从最基础的生活用语学起。一番努力后,我在路边摆起了一个投资最小的春卷摊。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,1谢克尔能兑换2元人民币,我的春卷摊每天能挣到十来个谢克尔,虽然不多,但这是我生活的希望。
孩子到来:碰撞中开启转变
1993年5月,春卷摊的生意逐渐稳定下来,我迫不及待地把3个孩子接到了以色列。可孩子们刚到这里,就遭遇了邻居们的责难。
在国内的时候,我一直秉持着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的原则,到了以色列,我依旧想做个称职的中国式妈妈。每天,我送孩子们去学校后,就守着春卷摊忙碌。下午放学,孩子们会来到摊前,我便停下手中的生意,在小炉子上给他们做馄饨、下面条,看着他们吃得满足,我心里也满是温暖。
直到有一天,当孩子们围在小炉子旁等我做饭时,邻居走过来,毫不留情地训斥老大:“你都这么大了,应该学会帮你妈妈,而不是在这儿干看着,像个没用的人!”说完,她又转头指责我:“别把你们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,不是生了孩子就自然而然成了合格的母亲……”这些话像锋利的刀子,刺痛了我和老大的心。回到家,我强忍着泪水安慰老大:“别往心里去,妈妈能行,妈妈愿意照顾你们。”可老大却懂事地说:“也许她说得对,妈妈,让我试试照顾弟弟妹妹吧。”那一刻,我既心疼又欣慰。
第二天是祈祷日,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。他们来到春卷摊,老大主动坐在我旁边,认真地学着我的样子,包春卷、下油锅。一开始,他的动作十分笨拙,手忙脚乱的,但随着一个个春卷下锅,他越来越熟练。我看着他的样子,心里满是惊喜。
不仅如此,老大还提议带着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。从此,每天早上,他和弟弟妹妹每人都会带着20个春卷去学校。放学回来时,他们会把卖春卷挣的10谢克尔全部交给我。看着他们小小的身影,我满心心酸,这么小的年纪就要承受生活的压力。可孩子们却没有丝毫抱怨,反而兴奋地说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,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,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。
犹太教育:理念重塑成长轨迹
邻居太太经常来找我聊天,跟我分享犹太家庭的教育方式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,“赚钱从娃娃抓起”,就像我们中国人重视孩子的教育一样,他们认为让孩子从小接触赚钱是最好的教育。
在犹太家庭,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,所有东西都有价格,孩子们必须学会赚钱,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刚开始,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太残酷,心里有些抵触。但孩子们在学校也接受着同样的理念,他们比我更容易接受这种犹太法则。思索再三,我决定改变以前在中国的教育习惯,试着培养孩子们适应这里的生活。
于是,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。在家吃一顿饭,需要支付100雅戈洛的成本费;洗一次衣服,要付50雅戈洛……同时,我也给他们提供赚钱的机会,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格批发给他们,他们带到学校后,可以自行加价售卖,赚的利润归自己支配。
第一天下午,孩子们回来后,我发现他们卖春卷的方式各不相同。老二比较实在,按照50雅戈洛一个的价格零售,赚了400雅戈洛;老三则采用批发的方式,以40雅戈洛一个的价格把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,虽然利润只有200雅戈洛,但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,这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。
而老大的做法最让我惊讶。他在学校举办了一场“带你走进中国”的讲座,自己担任主讲人,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。讲座的亮点是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,但需要购买10雅戈洛一张的入场券。他还把每个春卷精心分成10份,这场讲座吸引了200个听众。扣除上缴学校的500雅戈洛场地费后,他竟然赚了1500雅戈洛!
短短几天,孩子们就像变了个人似的,从只会撒娇的孩子变成了精明的小商人。更让我惊喜的是,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受到影响。为了想出更多新奇的赚钱方法,他们学习更加努力,思考也更加积极。学校老师的授课内容也很对他们的胃口,没有那些空洞的说教。老师曾问过他们一个问题:“当遭到异教徒袭击,必须逃命的时候,你会带什么逃走?”答案不是“钱”,也不是“宝石”,因为这些一旦被夺走就一无所有了。正确答案是“教育”,只要人活着,教育就不会被别人抢走。老师还说:“如果想将来成为富翁,就要学好眼前的知识,它们以后都会派上大用场。”孩子们对这些话深信不疑。
成长收获:各自绽放独特光芒
老大在法律课上学到了移民法的知识,他兴奋地告诉我,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。我半信半疑地去了,没想到真的领回了6000谢克尔,这对我们家来说,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之后,老大跟我说,因为是他提供的信息,我应该付给他10%的酬金。我犹豫了很久,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但看着他期待的眼神,我最终还是把600谢克尔给了他。老大拿到钱后,没有自己独享,而是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漂亮的礼物。剩下的钱,他说要拿去赚更多的钱。他用这笔钱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,拿到学校去卖,赚了钱又继续进货。一年后,他账户上的金额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。
虽然老大很会赚钱,但老二对犹太法则的理解似乎更深刻。犹太人擅长从事不需要投入本钱、别人又不做的行业。老大利用国内资源赚钱时,老二则在精神领域开辟了自己的“赚钱天地”。14岁的他,凭借出色的文笔,在报纸上开设了专栏,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。每周交稿2篇,每篇1000字,每月能挣8000雅戈洛。
老三是个文静的女孩,在赚钱方面没有两个哥哥那么突出,但她却展现出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。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,每天晚上,她都会精心煮一壶红茶,配上自己独创的点心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点心,聊着天,温馨极了。老三做的点心融合了中西风味,两个哥哥都特别喜欢。当然,这些点心可不是免费的,扣除成本和交给我的费用后,老三也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,生活得很滋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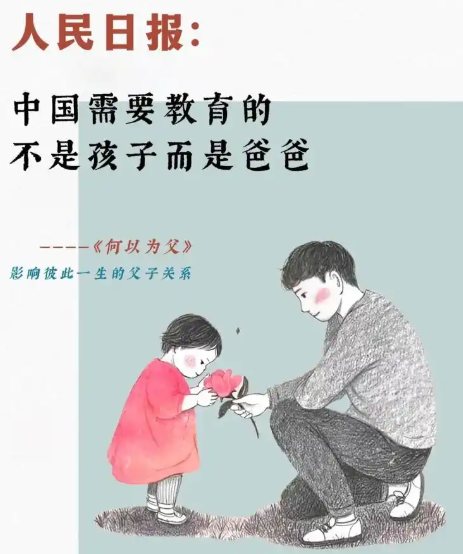
家庭发展:从以色列到中国的成长跨越
随着孩子们的努力和家庭收入的增加,我们一家四口合资开了一家中国餐厅。我占40%的股份,老大占30%,老二占20%,老三占10%。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,名气也越来越大,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关注。后来,我有幸获得了拉宾的接见,一下子成了以色列的名人。凭借着熟练掌握的希伯来文和母语中文,我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,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。
于是,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中国。回国后,我发现孩子们的成长远超我的想象。在回国前,他们买了很多以色列的特色物品。回到中国后,学校老师找到我,说我的孩子在校园里推销以色列的商品,从饰品、民族服装到子弹壳,五花八门,希望我能管管。我告诉老师,我不会干涉孩子们的行为,这是他们赚取学费的方式,因为我已经不再承担他们全部的学习费用。老师瞪大了眼睛,她无法理解月薪5000美元的我为什么不给孩子学费。我笑着请她品尝女儿做的小点心,每个在家只卖2元,然后说道:“这就是孩子们在以色列生活几年,学习犹太法则的成果,我相信他们以后都会很有出息。”
后来,老大考上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,他立志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,还要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旅游公司,垄断中国游业务;老二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,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,用文字创造财富;老三说要学习中国厨艺,成为顶级的糕点师,在以色列开一家最好的糕点店。
教育反思:中犹观念的差异与思考
回国后,我看到很多中国父母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。他们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富翁,过上富足的生活,又害怕孩子过早地接触金钱,沉迷其中;就像既期待孩子能拥有幸福的家庭,又担心孩子早恋影响学业一样。
这就像“叶公好龙”,犹太人从孩子出生就培养他们的赚钱意识,赚钱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目标,而教育、学习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。相比之下,中国父母虽然心里也有这样的期望,但却很少主动和孩子谈论金钱这个话题。其实,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,真的有那么难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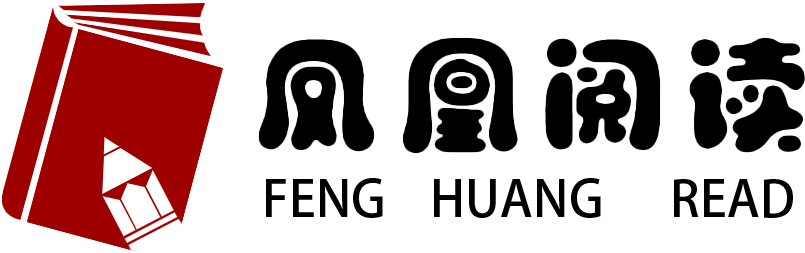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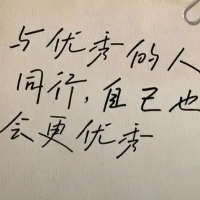
评论